张晓刚:“不那样去画心里就会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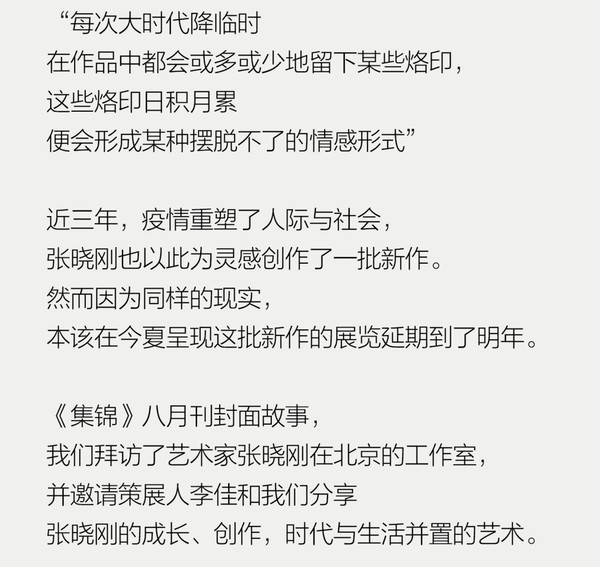
照片是不久前拍摄的,张晓刚站在夹着白纸的画架前,画室的另一面墙上贴满了各种图片素材和小稿,已经完成的那些新作则排列在画室空间的纵深里,尚未被更多的人看到,还保持着新作品的神秘性。灵感墙——白纸——作品,在这三点之间移动或不动的画家本人,像一个熟知所有劳作过程的搬运工,这过程也包括面对白纸的大量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劳作,或休息,世界如斯,紧密松驰,比起面对新的图画,画家面对白纸,这是一个更丰富的瞬间。

工作室的一面墙上贴着张晓刚收集的各种素材。
今年4月到7月,我一直都在上海。半年前,我正在张晓刚的画室里,讨论上海龙美术馆的展览计划,猫咪大卡盘踞在桌面摊开的笔记本上,桌下躺着它的孪生姐妹小卡。张晓刚带我们走过在墙上排开的,刚刚完成的新画,用他特有的那种缓慢、简练的语气,谈起他想象中这个系列的展现方式:像打开一本日记,或进入一条幽长的图像走廊,让看画的人跟随一道在画面中穿行的光,走回到自己内心幽深的地方。一个月后,疫情让分处两地的我们只能隔着屏幕会面、交谈,困居上海的焦虑,让我的时间感同现实脱节,展览计划依然在推进,但人与人的相隔,各自缩小在失速的空间,正在发生的现实好像也策应了这批作品的意涵,我们成为时空中的他者,而画面就在四周,每一天发生、上演。
也许是巧合,也许不是:这批即将展出的新作,灵感正是源自2020年初那段居家的日子。在一篇自述中,他写道:“我知道自己不具备将现实事件迅速转化成作品的能力……但之后会看到每次大时代降临时在作品中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某些烙印,这些烙印日积月累便会形成某种摆脱不了的情感形式,不论你是去画一张脸一把椅子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灯泡,它们都似乎被魔鬼附了身一样,成为某种魔幻的组合,永远存在,不那样去画心里就会不安,就会觉得那只是一具空壳。”在文末,他引用了卡夫卡的一句话:人不是从下往上地生长,而是从里向外地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


张晓刚工作室内。
一组被他命名为《蜉蝣日记》的纸上油画新作品,描绘了一个介乎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房间,来自不同时空的人、动物、家具和神话形象于此共存,似是而非的事物被看似合理地组合在一起,像是房间主人的臆想与幻梦,又像一出神秘的舞台剧。张晓刚清晰、精细地刻画出门窗、地板、静止的吊扇、摊开的书、浴缸里的电视、散落地面的扳手和刀剪、盛在洗手池里鲜艳的生肉、被口罩蒙住头部的小狗、套着颈圈的猫……偶尔出现房间中的人孤独迷惘,仿佛犹在梦中。时有闪现如戈雅或格列柯等古典大师笔下梦魇一般的形象,或宗教绘画特有的色彩、光线和氛围。即便这些意象如此纷繁复杂,对张晓刚来说,它们都是来自人生中某阶段的经历,以及它们萦绕不去的回响、逝去岁月的片刻闪现、过往记忆投下的影子,或他每日与之相对的现实物事。或许对他来说,绘画同时也是一种最孤独的书写,在这个被拉长至无穷向永恒延伸的过程之中,一些东西沉降更深,一些东西慢慢浮起和释放。绘画的平面和书写的平面在此交汇合一,时间和地点、记忆与历史、人、物与事,往昔、此刻和未来,在这里游动、闪亮。

《蜉蝣日记》以纸上油画为表达语言,一部分是重拾和延续张晓刚从创作生涯早期即已发展出的一条成熟而极富个人风格的脉络:即以硬笔造型刻印线条,固定画面再渗透油彩,以获得更自由和更富表现力的画面。但更多则是考虑到纸张作为媒介在形式、肌理、文化意蕴和引发心理联想方面的潜力。白纸既是图像的基底,也是书写和记忆传递的载体。
手撕纸张形成的特殊效果,将不同形状、质地的手撕纸片拼贴或叠加为图底,再根据组成画面的纸基局部形成的张力、走向或心理联想绘制不同的物体与人物,形成分裂又重合的,具有荒诞意味的矛盾体。来自不同时空的人和物通过拼贴被暂时地汇聚在纸面形成的虚拟空间之中,而这个空间本身的物质基底已经是破碎的,分裂的,但又以高度自由的方式被汇聚和弥合在一起。张晓刚在背景上加入各种类似手撕或刻画的格子形状,以及锯齿状的碎片效果,像是瓷砖,又像是空白笔记本的方格,也像孩子们玩的拼图游戏。而纸张边缘被刻意保留的手撕痕迹、层次和质地,经过拼接、刻印、堆积等处理之后,仿佛提供了一种有关时间的信息。张晓刚以这种方式释放了对于表达时间的焦虑。

张晓刚在书房中。
时间在他的心灵中曾经投下一道最长的影子。1958年,张晓刚出生在动荡的岁月中,经历了同家人的分散,孤独和不确定感逐渐成为他内心世界的底色。1976年高中毕业后,他经历了上山下乡,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成为当时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他不满足于服从学院体系推行的那一套由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的艺术风格,努力探索自己的路:毕业后,他做过灯泡厂的工人,也做过舞美设计师,经历过绝望,低落,同酒精为伴,死亡擦肩而过,又一次带着重燃的希望投入“八五新潮”的集体振奋和勇往直前。
在1991年一封给批评家栗宪庭的信中,张晓刚写道:“我们也许真该感谢我们所身处复杂多变的‘现实’,正是那许许多多的‘现实’使我们逐步地从浪漫的情怀和空虚的理想主义中觉醒过来,以艺术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现实,面对那些在寂静的深夜里哀号的灵魂。”
很快,他发现灵魂的形象竟是他最熟悉的样子:1993年回成都老家探亲时,张晓刚偶然在家中的相册里发现了一些泛黄的老照片,他惊讶地发现照片中的母亲如此年轻美丽,与他童年记忆中的形象完全不同,从这张老照片开始,他在脑海里重新构想了一段历史,既是个人的体验,家庭的记忆,也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和遭际。1994年,他创作出了“血缘:大家庭”系列的第一批作品,它们在随后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也为艺术家奠定了“国民画家”的声誉。



“血缘:大家庭”系列
今天,这批作品几乎已经成为代表特定年代中国人面貌的图像志。在这些以黑白照片上的家人为造型灵感的画面中,人的面孔或头像被放大,勾勒在浅淡的背景之上,他们看起来眉目与神情都十分相似,笼罩在一种似是由内渗透出来的朦胧之中。与之相对的则是用清晰笔触刻画的,烙印在脸上的抽象的红色胎记,以及勾连和穿过身体的,纤细曲折而绵长不断的红色血线。这样的形象仿佛飘浮在现实的图像和记忆的意象之间,它放大和强化的,恰恰是二者之间纠缠、追随而又相互否认和消抹的复杂张力:张晓刚深谙历史进程和心理历程、生存现实与心灵真实、集体叙事和个人述说之间存在的缺口、断裂、抵牾、似是而非和荒诞的错位,哪怕是深藏内心的记忆也将在流转中不断经历修正和重写,他挥动画笔不是要去迎接一个时代,而是浅浅扫开心灵上沉积的一层灰,让这个时代,以及它的过去和未来所投下的全部影子更清晰地显现出来。

张晓刚与他收养的流浪狗。
从2002年开始,张晓刚从对人物的描绘进入到对与人相关的物件的描绘。一些同书写、阅读或记录相关的意象,如墨水瓶、灯、笔、电视机、沙发、笔记本和书等,开始成为他反复描绘的对象,并牵引出关于记忆、遗忘与失忆的探讨。这些静物意象在2008年前后开始的“绿墙”和“里与外”系列中,汇集和发展为在画面上组构一个心理空间的基本要素。从那时起,张晓刚尝试用朦胧而冷静的笔调,塑造一系列虚幻而主观化的、介于私密和公共、家庭和集体生活之间的,不确定的场景。在这些画面中,带有特定历史气息的静物(老式沙发、长椅、灯泡、军大衣)和无人的室内场景占据了主体,它们因艺术家的想象与愿望蒙上了一层仿佛失焦的、柔和而模糊的色泽。而它们背后则永远伴随一道带有岁月特征、勾连起社会主义集体记忆的绿色墙围。这个虚拟的空间,正如心理学家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所指出,只能是一个心灵的空间,它保存着我们在世界之中的经验,存在于真实和想象之间,只有在这里,人才能在创造性的游戏中找回自己。

张晓刚在工作室内。
像张晓刚这一代人,在短短几十年中经历了大时代的急风暴雨,仿佛从一场乌托邦的集体梦魇中醒来,面对形形色色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涌入与撞击,生活和心灵的双重震荡尚未平息,就被推挤着踏上这辆后社会主义时代高速奔驰的全球化列车。如果说时代教给了他什么,那也许恰恰是学会面对和相信自己的内心,深潜,向下,在最幽深晦暗的心灵空间辨认、读取和开掘那些尚待命名的形象和意象,通过绘画的动作来铺开一道通向它的窄门。也许,如果画家们愿意,他们本可以画出任何这个世界上有的或没有的东西,想到的或想不到的东西,而对张晓刚来说,画家只能画他们真正想画的——那个心灵最深处的结构,那个汇集了过去与现在、记忆与遗忘、“我”与“非我”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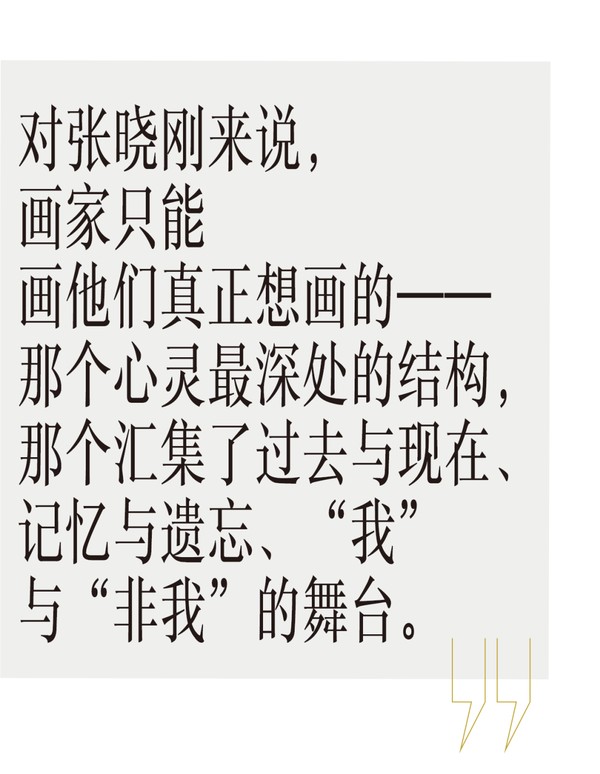
回到2020年春天,与最初几张《蜉蝣日记》差不多同时,张晓刚完成了他的《舞台3号:城堡》,一张长6米、高2米的大型油画。将近十年的时间,这张画一直默默立在他工作室的一面墙上,经历反复的修改,打磨,逐渐接近艺术家心中的理想:在绘画平面上创造一个看似真实又充满悖谬和荒诞的世界,一个梦与现实之间的临界状态,它的每个部分都要能够独立成一个画面或叙事,同时又能彼此产生张力,形成一个复杂的,包含不同中心,又是完整和自足的视觉结构。
“就像音乐中虽然用了各种乐器和声部,但最后还有个主题,把这些乐器的声音串在一起。”张晓刚说。
《舞台3号:城堡》描绘了一个像是风景,又像是舞台的空间,一座发光体一样的明黄色建筑占据地平线中央,立在远景的群山和中景的河流之间,前景排布着一些悖谬又似有寓意的形象:一面映出军大衣的镜子,一截断手,邮筒,闭目起跳的男子,戴眼镜的女孩和有男孩身体的狗头并坐在一个浅盘里,蒙住双眼的青年骑在马上,脸朝向画幅结束的方向。画面两端伸出像是墙壁或屏风的块面,暗示人们从此进入一个介乎无边界的连续风景和封闭的室内舞台之间的、暧昧的阈限空间——形象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总处在某种非确定的过渡状态,但又因此摆脱了既定意义的桎梏,向一些依稀未知的方向敞开。
这些年来,张晓刚一直在摸索着如何用绘画去搭建这样一个世界和舞台:艺术家在其中像是建筑师,又像是电影导演,用来自不同时空的局部慢慢搭建起一个恢弘又虚妄的空间——一个史诗般的寓言空间,同时也是属于个体的,由记忆和情感填充的心灵空间。心灵就像是那个在张晓刚的绘画中反复出现的,最熟悉、最秘密而又时时投下陌生阴影的房间,也是包容一切可能与不可能、一切已逝、未有和将至的舞台。像艺术家自己所说,在这样一个心理空间中,时代也好,生活也好,都并置在一起,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感觉”。

本文刊登于《The New York Times Life and Arts集锦》八月刊
